技术革命的专利法答卷——评《人工智能时代的专利法研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深教授、文澜学者,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吴汉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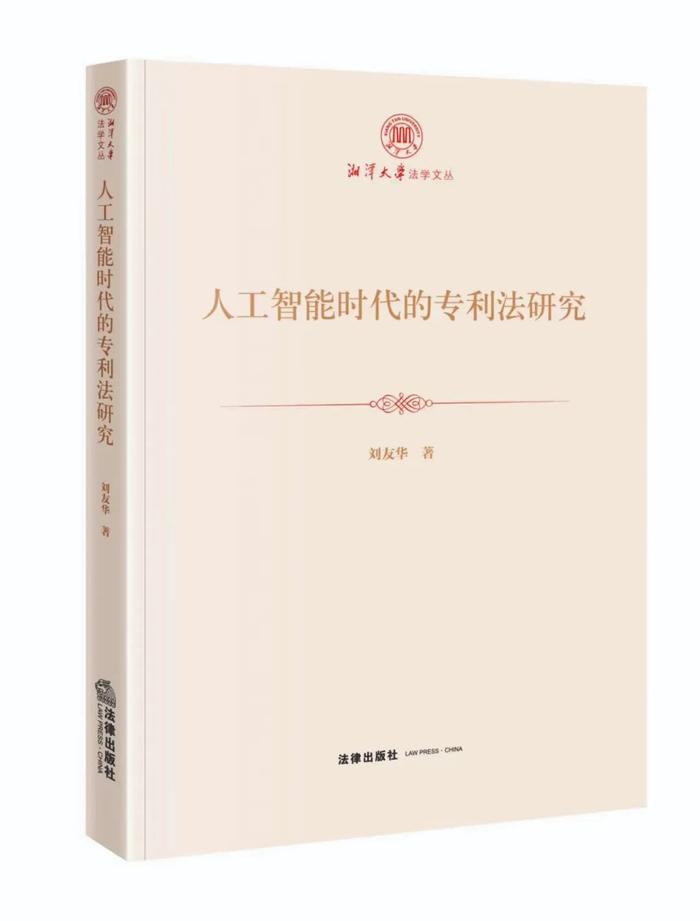 >>刘友华著:《人工智能时代的专利法研究》
>>刘友华著:《人工智能时代的专利法研究》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加速了发明创造的进程。人工智能既可能辅助发明人或与发明人合作生成新发明,未来也可能具有独立生成技术方案的能力。对此,专利法应当对如下问题作出回应:人工智能对其生成的发明能否作为专利主体、谁是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发明人和专利权人、人工智能生成发明对专利授权判断标准的挑战等。技术革新与制度变革之间存在良性互动,作为激励和保护创新的专利法,一方面,是科技进步与要素创新的平衡器,其制度设计直接影响相应主体的激励;另一方面,技术飞跃促使专利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此作出回应。因而,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专利制度如何回应既是重大理论前沿问题,也是极为重要的实践问题。
面对创新激励与产业发展需求,湘潭大学刘友华教授的《人工智能时代的专利法研究》可谓恰逢其时,系统回应了笔者提出的“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专利法之问”,并在此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和思考。刘友华教授十余年来潜心研究新技术对知识产权法的影响,该书展现了刘友华教授对人工智能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思考,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人工智能对专利制度变革的著作,值得关注和推介。
该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清晰展现知识谱系,全面梳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及相关专利布局状况;二是及时回应人工智能对专利审查的挑战,基于深度的理论探究,剖析了人工智能对专利主体、客体、审查标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三是科学把握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的权属分配规则和侵权认定标准,为解决产业利润分配提供范式。全书内容翔实、框架明晰、论证充分、亮点颇多,立足产业发展脉络,详尽阐述了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现状以及相关专利布局。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工智能对专利法的影响与挑战表现不同,划分为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阶段,与人工智能不同阶段相关的专利大致分为:人工智能本身的发明、人工智能添加在已有设备中提升功能性的发明、人工智能用于创造新发明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的发明。通过专利检索与情报学分析,人工智能专利布局应立足于:机器学习技术、自然语音处理技术、图像处理技术、人机交互技术、人工智能芯片等,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专利申请呈持续增长、爆发态势,深度求索等大模型迅速发展表明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迅猛,但仍需强化产学研融合创新,加快人工智能全球专利布局。
人工智能是信息技术迭代更新的尖端科技,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可能冲击人工智能主体认定、客体范畴、专利授权规则等专利制度。在恪守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从人工智能不具有法律主体资格的角度论证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的辅助作用,而人工智能生成发明挑战了专利制度中的专利主体、专利排除客体和公共秩序。因而,应开放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专利主体,可设置较严格审查标准,认可人工智能算法的主体适格性。同时,加强人工智能相关发明的公共秩序审查,现阶段涉嫌侵犯个人信息、可能威胁人类社会、涉及算法偏见的人工智能发明应作为专利排除对象。
人工智能时代带来专利申请数量的急剧增长,专利审查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标准需作出调整。新颖性审查标准决定可获授权技术方案的数量与质量。就新颖性审查而言,明确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现有技术范畴,从平衡与激励视角下明晰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方案的价值导向。对实用性审查,应严格区分“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审查与信息充分公开,将“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审查置于前端;同时,强化“能够产生积极效果”审查,引入风险审查和绿色原则,过滤存在伦理道德风险的申请。在创造性审查方面,一方面,“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的判断标准难以适配人工智能领域。作为拟制概念,要求专利审查员从所属技术领域内普通技术人员视角审查申请,但人工智能的生成过程提高了发明创造的门槛,抑制自然人创新。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将打破原有技术领域界限,其跨库检索能力,可整合多技术领域进行知识组合,将挑战技术人员的“所属技术领域”。因此,可通过创造性判断要素客观化的方式提高创造性审查标准和高度;重新拟制技术人员概念,采用熟练技术人员标准而非发明机器标准,将参与创新的人工智能水平仅作为创造性判断标准,即活跃工人使用的技术;打破技术领域的界限范围,综合人工智能与自然人的视角审查创造性,应用大数据等手段辅助审查。
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权属分配决定了产业激励模式,急需对其权利归属作前瞻性回应。其中判断人工智能发明创造过程中各方主体创造性贡献是关键因素。人工智能参与或独立完成发明创作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与自然人共同完成发明;二是强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独立完成发明。第一种情形中,人工智能作为一项辅助性技术参与发明,人工智能发明过程中涉及数据提供者、研发者、所有权人、使用者等主体,数据提供者起到辅助作用,研发者对算法贡献作出创造性投入,所有权人具有投资人地位,使用者则属于发明过程实施者。可根据贡献度大小,坚持“法定优先、约定例外”原则确定权利主体。第二种情形中,强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自主生成发明,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发明的创造性贡献度降低甚至没有,将权利赋予利用和开发最有力的主体即人工智能使用人,通过产权激励促进创新。
人工智能在发明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日益增大,从机器辅助演变为人机合作,人工智能逐渐从辅助工具向自主创造转变,给专利制度主体理论带来挑战,表现在主体资格问题、人工智能相关主体的利益分配等。达布斯人工智能系统案表明,各国总体上坚守人工智能不具有发明人资格,这也是对产业发展的反思。通过研究认为,在超人工智能到来之前,仍应坚守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不宜赋予人工智能以民事主体资格,应限定发明人为自然人。同时,应基于诚信原则与公平原则披露人工智能在发明创造中的作用,以区分技术方案完成人以及区别专利审查标准;在发明创造过程中遵循人类“最小贡献”要求,并随技术发展而适当降低。
总之,《人工智能时代的专利法研究》一书作为人工智能专利法领域的开拓性之作,基于技术革新与法律变迁视角,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对专利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挑战,就我国相关专利授权审查规则提出了应对策略,兼具实践性与前沿性,为相关立法完善提出了体系性框架,并对专利制度变革提出了可操作性规则。在全球竞争视野下对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专利布局和产业发展具有较强借鉴意义。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5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