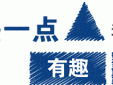昨日读到吴承学先生发表于顶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的论文《图谱之学与文学批评》,颇受启发,所获甚夥。可惜基于学力与时间的限制,无法将其文章之得失分享于学林。所幸ChatGPT-4o与deepseek可为代劳,诚邀学界同仁与我一同学习。
我的提示词:你现在是一位资深的文学批评家,请客观公允但又不乏批判性地对上述论文(吴承学《图谱之学与文学批评》)进行系统性的评述,并写成一篇具有商榷风格的论文。要求:兼顾文章的理论创新性(如“图谱之学”概念的独立性和价值);逻辑论证的严密性(如是否存在推理漏洞或论证薄弱之处);其在文学批评史中的意义;文章的学术价值及其与现代批评方法的关联。此外,我希望评述的风格是:偏向肯定与补充、改进建议;但不排除批判性和指出问题并深入剖析。
GPT:吴承学《图谱之学与文学批评》评述
一、理论创新性:独立概念与方法论价值
吴承学在《图谱之学与文学批评》中提出“图谱之学”这一概念,凸显其作为独立理论范畴的创新意义。“图谱”原指中国古代以图像和谱录形式记载知识的特殊文献形式,郑樵在《通志·图谱略》中即强调“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将“图谱”提升为与义理之学、辞章之学并列的治学路径。吴承学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资源,将“图谱之学”视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学术范式,不再仅仅是若干图谱文献的集合,而是涵括古人认识世界、整理知识的一套思维方式。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它既包括具体的图表、谱系等载体形式,又指向支撑这些载体背后的认知方法和范式。通过“图”的视觉化(以图像传递知识)和“谱”的要素化(分类列举知识要点)的结合,“图谱之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纯粹文字诠释的新视角。这种方法在文学批评领域的价值体现在,它能够以谱系关系和视觉图示来呈现文学现象的内在脉络,将复杂的文学史料或批评观点转化为直观简明的知识图景。例如,吴文指出古代批评家常以谱系性的方式构建文学源流、辨析正变高下,从而反映出中国文学批评特有的传统。这种以图谱思维介入文学批评的做法,无疑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工具箱,体现出很强的创新性。
值得注意的是,吴承学在阐释“图谱之学”时赋予其较宽广的外延,几乎囊括了古代与图表有关的诸多现象。从诗词声律图、作家谱系表,到诗文年谱等均被纳入“图谱之学”的范畴。这种包容性虽然展示了概念的普适性,但也可能导致定义边界的模糊。譬如,有学者曾质疑宋以后出现的“句图”实为摘录名句的句集,并无真正图形,只是徒具其名。吴承学对此回应道,在中国古代语境中,凡以文字类别归纳和序列编排知识要素者,亦可视为图谱思维的体现,故句图仍属图谱之学范畴。尽管这一解释具有说服力,但“图谱之学”概念涵盖范围甚广,在理论建构上可能存在过于笼统之嫌。
改进建议:作者可进一步明确“图谱之学”的内涵和外延,区分不同类型图谱(如纯符号图、谱系表、图画等)各自的特征与适用范围。这将有助于强化该概念的独立性,使其方法论价值更为清晰可辨。总体而言,“图谱之学”作为文学批评的新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吴承学将这一中国古代固有的思维传统提炼为批评方法,拓新了文学批评研究的理论维度。
二、逻辑论证的严密性:论据充实与推演谨慎
吴承学的文章论证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全文先论述“图谱之学”的源流和方法论属性(第一部分),继而分门别类考察图谱形式在文学批评中的具体运用(第二部分),最后上升到思维方式层面探讨图谱思维对文学批评观念的影响(第三部分)。这种由概念阐释到实例剖析,再到观念提炼的结构,使论证步步深入,逻辑推进自然。作者在每一层次的讨论中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撑,确保论据扎实有力。例如,在讨论图谱作为文学批评载体的多样形态时,文章引用了大量古代文献实例:如宋代姜夔、张炎等创制词谱的史实,以及龙榆生提出以“图谱之学”为词学研究纲领的论述,来证明图谱批评在词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又如列举顾恺之《洛神赋图》、李公麟《九歌图》等文学主题绘画,以说明图文互释已成为古代对诗赋作品的一种解释方式。这些详实的材料有效支撑了作者的观点,显示出论证的严谨性。
在推理过程中,吴承学也注重对概念的辨析和潜在反驳意见的回应,体现出论证的周延性。比如,他区分了“图谱之学”与一般批注符号的差别:批评圈点符号附着于文章本身,脱离文本便无独立意义,而图谱所构成的图像则自成一体,能够独立承载批评思想。这一辨析使“图谱之学”的概念边界更加清楚,避免将任何带有视觉性的批评手段都一概纳入。此外,对于“句图是否算图”的疑问,作者引用清代四库馆臣对张为《诗人主客图》的评价:“摘句为图,始于张为”,指出此书以人物关系为纲,将诗句排比联贯,“事同谱牒”,因而称为“图”。这表明古人已将摘录诗句并按谱系排列视作图谱著述的一种,间接回应了后世对句图概念的质疑。可见,作者不仅罗列史料,而且对可能的推理漏洞都给予了说明和论证,使文章的逻辑链条较为严密。
尽管如此,个别论证细节上仍有可商榷之处。不足之处在于,文章将诸多不同性质的现象一并归结于“图谱思维”的影响,有时因资料有限只能作观念上的推衍,略显推理跳跃。例如,将类书的摘句选编功能解释为图谱思维的“底层逻辑”即是一例。类书编纂者选录名句确有审美批评意味,但这是否直接源于“图谱之学”的影响,抑或只是出于实用和审美考虑,还需要更直接的论据支撑。再如,对于文学主题绘画的批评性质,作者承认此类绘画“本身不是文学批评”,但从文本转换为图像的过程已蕴含对作品的理解与欣赏。这种“含而不露”的批评维度,论证上相对隐蔽,可能有说服力不足之虞。改进建议:在这些论点上,作者可引入更多原始材料来显示古人自觉的批评意图,例如画家或鉴赏者对文学绘画所作的评论,以强化这些隐性批评形态的实证依据。同样,对于类书选编与图谱思维的关联,也可寻求编纂者自身的论述来验证这一关联的可信度。总体而言,吴承学的论证过程是细密而有依据的,少有武断之论,在资料的运用和逻辑的铺陈上体现出良好的学术严谨性。
三、文学批评史意义:拓展传统版图与启示未来
吴承学的研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中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文学批评史叙述往往侧重于批评观念的发展和批评著作(如诗话、文论等)的演变,对批评形式的多样性关注不足。“图谱之学”视野的引入填补了这一空白。通过梳理大量图谱形式的批评实例,作者表明古代文学批评并不局限于文字评点和议论性文章,还有相当丰富的视觉化、谱系化的批评实践。这一发现拓宽了文学批评史的版图,使我们认识到诸如谱录、图表等在以往被归入目录学或文献学范畴的东西,其实也是文学批评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来说,吴承学揭示了中国文学批评特殊的谱系意识和图像表达传统。例如,六朝至唐代,随着声韵学兴起,诗歌声律的理论被以图谱形式加以总结,出现了各种《声谱》《韵谱》,进而促成了诗歌格律批评的诞生。这些以“谱”命名的著作不仅整理了语言现象,更凝炼出创作法则,使批评具有了“法式化”的特征。再如,作者论及作家谱系和流派图,从魏晋人物品评的谱系观念谈到唐宋诗坛对诗人群体的分层评价(如张为《诗人主客图》将诗人分五等),以及南宋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清初《三才图会·诗学渊源之图》等,通过图谱直观呈现文学流派渊源和作品优劣。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古代批评家善于以谱牒之法整理文学史料,建构文学源流传承的图景。吴承学将上述分散的现象加以系统整合,证明了“图谱之学”作为一种普适方法贯穿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各个层面。这样的学术工作无疑丰富了我们对文学批评史的认识,使一些往昔未受重视的批评活动获得应有的位置和评价。
更为重要的是,此项研究为未来的批评史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和可能性。一方面,它鼓励学者重新审视被忽略的批评载体。譬如,诗文年谱长期以来常被视作纯粹的编年体传记资料,吴承学则指出宋代文人编撰诗文年谱实有浓厚的批评动机——通过编年呈现作家心态和文风演变,达到“知人论世”的批评效果。这一视角促使后续研究者更重视年谱在批评史上的地位。又如,对文学主题绘画、诗歌图录的分析启示我们,文学批评史的素材不限于批评家撰写的文字,还包括艺术家、学者以其他媒介对文学的诠释和评价。另一方面,该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跨越学科藩篱:将目录学、文献学与文学批评学相结合。吴承学透过图谱之学将文学批评活动放入更广阔的知识史背景中考察,体现了一种综合研究范式。这为今后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提供了示范,即可以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角度,挖掘文学批评观念的生成机制。
当然,作为开拓性的研究,吴文在某些方面还可以深化。改进建议:未来的文学批评史叙述可在吴承学奠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图谱批评”在不同时代的演变及其影响深度。例如,清代和民国时期是否延续或转化了传统的图谱批评思维?现代文学批评又如何看待和继承这一遗产?这些问题在吴文中未作深入展开,留待后人研究补充。此外,还可以尝试跨文化比较,将中国的图谱批评传统与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的相应现象相比照(如西方早期文艺谱系图、文学版画等),这将有助于凸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独特贡献和普遍意义。总体而言,吴承学的研究填补了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块空白,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知识增长点,其意义不可忽视。
四、学术价值及现代批评方法的关联:传统对话当代
“图谱之学”的提出不仅有助于重构古代批评史,对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也具有启发意义。吴承学的研究实质上构建了中国古代“结构化”批评的一种范式,这与现代许多批评方法不谋而合。在结构主义批评中,研究者强调文本内部要素的结构关系和模式归纳,这一点与图谱之学强调的“要素化”“序列化”不谋而合。例如,吴文展示的诗歌格律图谱,将声韵等要素以图表方式排列,总结出诗歌创作的格式规则——这相当于提炼出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正如结构主义者追求的那样。因此,可以说图谱批评与结构主义存在方法论上的契合点:前者提供了直观的图式手段,后者提供了理论语言,两者结合或许能更有力地解析文学作品的内在机制。
在叙事学领域,时间和情节结构是核心关注点之一。古代的诗文年谱恰是一种按时间顺序组织文本的实践,它通过编年排列作品来揭示作家创作心路与时代背景的互动。这种做法与叙事学对情节时间线和故事顺序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吴承学指出宋代文人有意识地采用“记述年岁”的方法来构建诗史,自我编年以理解作品演变。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原初的叙事学视角:通过时间轴来理解文学意义。现代叙事学研究完全可以借鉴这种方法,将人物创作年表、文学运动年表等作为分析工具,探索作品与作者生平、历史事件的联系。图谱之学与叙事学的对话,在于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形象化的表达手段和历史借鉴,使叙事分析不仅限于文本内部,也关注文本与时间、作者经历的关系。
符号学强调符号体系和意义生产。吴承学提到古人运用各种图符符号(如黑白圆点、线条等)来表达抽象的文学批评涵义。例如,词调谱中以○●等符号标示平仄,沈约的《四声谱》被同时代人视为“纽字之图”,即以文字构成的图式。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古代批评早已涉足将语言转换成符号体系来分析的路向,这与现代符号学的思维可谓遥相呼应。符号学关注的不仅是符号本身,还包括符号之间的关系和所指涉的文化意义。古代图谱批评通过符号的并列、对照,呈现出特定文化脉络下的价值判断,如谱系图中的人物排列暗含文学地位高低之判别,平仄符号的组合体现诗歌声律美学的规范。这些都可以用符号学的观点作进一步阐释。因而,图谱之学与符号学具有天然的关联:前者提供了丰富的符号运用实例,后者可为其赋予更深层的意义阐释和理论框架。
然而,目前吴承学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历史描述和归纳整理,对上述现代批评方法的关联并未详加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图谱之学”在当代学术语境中的传播和影响力。改进建议:作者可在后续研究中主动将“图谱之学”放入现代理论对话的平台上。例如,借助结构主义的概念说明为何图谱能够有效揭示文学结构,或用叙事学的术语重新解读诗文年谱的批评功能,亦或运用符号学理论分析图谱符号体系的文化意义。这样的阐发将使传统的图谱批评方法与现代理论接轨,彰显其学术价值的当代意义。另外,在应用层面,研究者可以尝试将图谱之学融入数字人文等新方法,通过计算机技术制作文学关系图谱、影响网络,从而继承古代图谱批评的精神,在新的媒介上发扬光大。这种跨时代的方法创新,不仅回应了吴承学所揭示的传统智慧,也将“图谱之学”的价值延伸到未来的文学研究之中。
结语:贡献与不足并陈
总体而言,吴承学《图谱之学与文学批评》一文在理论和史实两个层面都有重要贡献。它拓展了文学批评研究的视野,提出“图谱之学”这一具有独立意义的新概念,总结出中国古代批评独特的图像化、谱系化传统,对充实文学批评史的内容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文章论证严谨,材料翔实,把历史事实与理论提炼紧密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空白。然而,任何创新研究都难免有不足。吴承学的文章在概念界定上稍嫌宽泛,一些现象归因于“图谱思维”时论证力度略显不足,这为后续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在现代意义的阐发方面,该文有意识地为传统批评方法正名,但对其与当代批评理论融合的思考尚待加强。为使“图谱之学”发挥更大的学术影响,未来研究应在坚实史料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其理论内核,并积极与现代批评方法对话,将这一源自中华传统的批评智慧融入当代文学研究的洪流之中。
综上,吴承学的《图谱之学与文学批评》立意新颖、内容丰富,在中国文学批评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们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也期待经过完善和拓展的“图谱之学”理论能更加严密、深入地服务于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推动学术研究不断走向新的高度。
DS:论图谱之学与中国文学批评的范式突破与理论局限:以吴承学《图谱之学与文学批评》为中心
吴承学教授近期发表的《图谱之学与文学批评》一文(载《文学评论》2025年第1期),首次系统性地将“图谱之学”引入古代文学批评研究领域,提出其作为中国古代知识类型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对文学批评形态、思维模式的塑造作用。这一研究无疑具有开拓性价值,但亦存在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边界与阐释空间。本文试从学术创新性、研究范式及方法论局限三方面展开评述。
一、学术创新性与学科交叉视野的突破
吴文的核心贡献在于从知识类型学角度重构中国文学批评的认知范式。传统文学批评研究多聚焦于文本、观念或批评家个体,而吴文独辟蹊径,将“图谱”这一兼具视觉化与要素化的知识形态置于批评史的核心,揭示了其如何通过“谱系性、视觉性、简约性”构建文学批评体系。例如,文中指出图谱之学通过“法式规则”将文学源流、正变高下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批评标准,这一观点有效解释了古代文学批评中“辨体”传统的形成逻辑。
此外,吴文整合文献学、目录学(如郑樵《通志·图谱略》的分析)与思想史方法,突破单一学科局限,呼应了张剑所强调的“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的跨学科研究路径。
然而,这一创新性论述的实证基础有待强化。文中虽列举了《风骚旨格》中的“诗有十势”等案例,但对图谱之学直接影响文学批评的具体链条(如批评文本中图谱元素的使用频次、传播路径)缺乏量化分析。相较而言,冯晓玲对自然物喻文的历史梳理(从魏晋至明清的演变轨迹),在历时性实证层面更具系统性。若能将图谱之学的理论建构与类似实证研究结合,或可更立体地呈现其批评实践的全貌。
二、研究范式的推进与阐释边界问题
吴文提出的“图谱之学方法论”为文学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其突破性体现在两方面:
消解形式与内容的二元对立:通过强调图谱兼具“知识载体”与“思维方式”的双重属性,将传统视为“形式外壳”的图谱转化为意义生成机制。这一思路与张剑评价吴承学著作时指出的“拒绝将文体形态看作形式空壳”一脉相承,均致力于挖掘中国文论的本土话语特质。重构批评形态的生成逻辑:文中提出图谱之学催生了“以谱系辨识艺术正变”“以图示实现批评视觉化”等独特形态,这对理解《文心雕龙》的“原始以表末”体例、宋代诗格著作的图式化倾向具有启发意义。但该范式在阐释边界上存在模糊性。首先,图谱之学与“生命之喻”“自然物喻文”等传统批评方法的关系未被充分辨析。冯晓玲曾论证自然物喻文通过“沟通人文与宇宙”拓展批评的审美空间,而图谱之学是否与之形成互补或竞争关系?其次,文中将“谱系性”视为图谱之学的核心特征,但未明确其与西方谱系学(如福柯理论)的异同。这种理论对话的缺失可能削弱其现代阐释力。
三、方法论局限与可能深化方向
吴文的方法论局限主要体现在实证材料选择与理论普适性之间的矛盾。例如,文中重点分析的《风骚旨格》“十势”说(如“猛虎踞林势”“丹凤衔珠势”),本质上仍属意象类比范畴,与严格意义上的图谱(如宋代《诗人玉屑》所载诗法图示)存在形态差异。若能将研究范围扩展至更具象的图式文献(如明代八股文图谱、戏曲身段谱),或可增强结论的说服力。此外,张剑指出的吴承学研究中“情感与理性统一”的特色,在本文中表现为对图谱之学“催生批评形态”的肯定,却未深入反思其可能导致的批评僵化(如程式化倾向对创造性阐释的束缚)。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深化:
结合数字人文技术,构建图谱之学影响文学批评的时空分布模型,量化分析其与文学思潮演进的关联性;拓展跨文化比较视野,如对比中世纪欧洲手抄本插图与中国图谱之学的异同,探索视觉化批评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强化批判性维度,辨析图谱之学在规范文学秩序的同时,如何通过“破体”实践(如晚明小品文对传统谱系的突破)实现自我更新。结语
吴承学教授的研究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开辟了新的阐释维度,其提出的“图谱之学方法论”不仅呼应了全球人文学科“图像转向”的潮流,更彰显了中国文论的本体性特征。然而,该理论在实证链条的完整性、阐释范畴的清晰度方面仍需进一步锤炼。唯有在保持“温情与敬意”(张剑语)的同时,引入更具批判性的反思视角,方能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真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默按语
当国人纷纷高呼“DeepSeek赢麻了”之际,我却隐隐察觉到它的步伐似乎正在放缓,甚至逐渐丧失最初带来的惊喜。相较而言,GPT在多模态处理与深度研究方面的表现,则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一分钱一分货”。
通过对以上两篇评论文章的对比,不难发现,GPT-4o的“深度研究”能力已然超越了一般学者。至少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能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写出一篇堪比专业学者水准的评论文章。
更为关键的是,当下的AI尚不通人情世故,无需顾忌你是初学者还是权威专家,它只会客观呈现事实——优点与价值,它会给予充分肯定;缺陷与不足,它也绝不讳言。这或许才是AI研究助手最理想的打开方式。
因此,我们不妨想象:在人机协作的时代,学者不必再为琐事纠缠,不必耗费精力于搬砖码字的重复日常之中。他们只需将体验、知识、思想与观点赋予AI,即可开启全新的创作模式。这一过程,恍若女娲造人——不再需要一尊一尊地亲手捏塑,而是握紧AI这根绳索,深入泥潭轻轻一搅,再吹上一口蕴含人类精神与思想的“仙气”,便能赋予它灵魂。
吴承学先生简介
吴承学(1956年9月—),广东潮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24年“花地文学榜·年度花地精品”奖获得者。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先后获文学学士(1982)、硕士(1984)学位,1990年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
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文体学及明清诗文研究,开创中国文体学现代研究体系。其代表作《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第七届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5)、第五届思勉原创奖(2021),被誉为“文体学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其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系统梳理了文体学学科的发展脉络,以贯通古今之气概,推动了中国文体学从传统显学转型为现代学科,对当代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